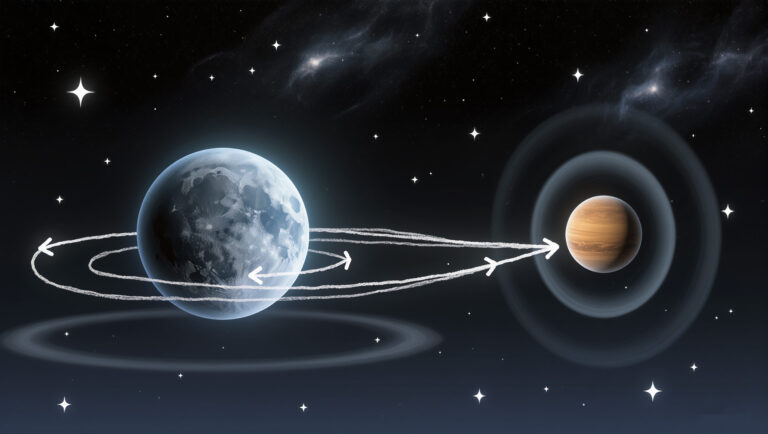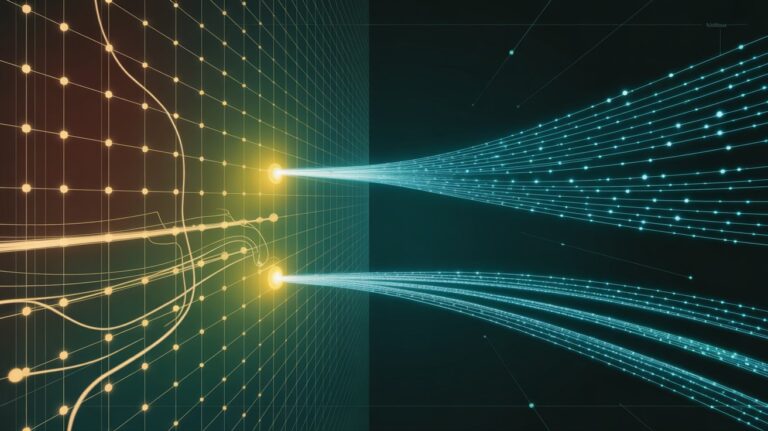【深造物理】大型強子對撞機:把宇宙縮進27公里的環形實驗室
如果要看清一件極微小的東西,你會怎樣做?用更高倍數的顯微鏡。物理學家也一樣,只是我們想看的「東西」小到電子、夸克這些基本粒子,顯微鏡已經幫不上忙。於是,我們造出一部「能量顯微鏡」——粒子加速器(particle accelerator)。當中的代表作,就是位於日內瓦附近、埋在地底約50至175米深的「大型強子對撞機」(Large Hadron Collider,簡稱 LHC)。它是一條周長26.7公里的環形隧道,把成束的質子(proton)加速到接近光速,讓兩道束流正面相撞,藉著高能量把自然界更深層的結構「照」出來。
為何要把粒子撞起來?能量就是解像度
要看見更細的結構,需要更短的探針波長。根據量子力學,粒子也帶有波動性,動量越大,對應的德布羅意波長越短,能「看」得更細。因此,把粒子加速到更高能量,就像把顯微鏡的解像度調高。相撞的時候,能量集中在極小體積,會短暫地轉化為各式各樣的新粒子,讓我們測量它們的性質與相互作用,檢驗標準模型(Standard Model)並探索其之外的物理。
LHC 是怎樣的一部機器?一覽關鍵規格
| 項目 | 數據(典型/設計) |
|---|---|
| 位置 | 瑞士與法國邊境地底 |
| 周長 | 約 26.7 公里 |
| 運行粒子 | 主要為質子(亦有鉛離子重離子運行) |
| 碰撞能量 | 設計 14 TeV (每束 7 TeV);現行 Run 3 達 13.6 TeV |
| 超導二極體磁鐵 | 約 1232 枚,磁場可達約 8.3 T |
| 運行溫度 | 約 1.9 K,以超流態氦(superfluid helium)冷卻 |
| 束團間隔 | 典型 25 ns (40 MHz 交會頻率) |
| 每束團質子數 | 約 1×10^11 |
| 束流能量儲存 | 每束可達數百兆焦(MJ) |
| 真空 | 超高真空,約 10^-10 mbar 級 |
| 設計亮度(luminosity) | ~1×10^34 cm^-2 s^-1;已達並突破 |
這些數字背後,蘊藏了冷凍工程、超導電磁學、超高真空、精密對準與控制論的極致協奏。
從氫氣到「近光速」:一束質子的旅程
LHC 並不是把粒子由零起步直接加速到最高能量,而是接力式的多級加速器鏈(accelerator chain):
- 氫氣經電離得到質子,由線性加速器 Linac4 打底加速。
- 注入質子同步加速器鏈:PS Booster → Proton Synchrotron (PS) → Super Proton Synchrotron (SPS)。每級都靠射頻腔(RF cavities)給每一圈一點「能量推力」。
- 最後從 SPS 經傳輸線注入 LHC 的兩條反向環形束道,分別逆時針與順時針運行。
- 在 LHC 內,超導磁鐵把束流彎起來「跑圈」,RF 腔(約 400 MHz)為粒子每圈補上電壓,逐步把能量推上多 TeV 等級。
束流並非連續,而是被切成「束團」(bunch)。每個束團像一小撮砂糖粒,裡面塞進大約一千億個質子。兩條束流以交錯時間表在特定位置交會,增加碰撞機率。
磁鐵、冷凍與真空:把大自然推到邊界
要讓質子在26.7公里的彎道以接近光速前進,需要強大的二極體磁鐵(dipole magnets)把它們彎回軌道,四極體(quadrupoles)與更高極磁鐵則用來聚焦束流,像光學鏡頭把光束收束。這些磁鐵以超導材料繞製,只有在極低溫才會零電阻運作。整個 LHC 使用了逾百噸的液氦,把磁鐵冷卻到約 1.9 K,比外太空的背景溫度還低。
束管內的氣壓被抽到超高真空,否則質子會不斷與殘餘氣體碰撞而散失。這就像在一條完全沒有空氣阻力的高速公路上駕駛,才能保持速度與秩序。
碰撞點上的「巨型相機」:四大實驗
LHC 的碰撞並不在隧道的每一處發生,而是在四個交會點,由四個巨型探測器(detector)「拍照」與「量度」。它們像超高階的3D相機,分層記錄粒子留下的軌跡、能量與種類:
- ATLAS 與 CMS:通用型(general-purpose)實驗,負責廣泛的粒子物理探索,包括2012年共同發現希格斯粒子(Higgs boson)。ATLAS 體積巨大;CMS 的溶液磁鐵(solenoid)磁場強達約 3.8 T,設計緊湊。
- LHCb:專注含 b 夸克的強子,研究物質—反物質不對稱(CP violation),解開為何宇宙幾乎沒有反物質的線索。
- ALICE:重離子(鉛離子)碰撞專家,重現早期宇宙的「夸克-膠子等離子體」(quark-gluon plasma),研究強作用力在高溫高密條件下的行為。
每個探測器都用內層矽像素追蹤器(pixel tracker)記錄粒子軌跡,用電磁/強子量能器(calorimeters)量度能量,外層以μ子系統(muon system)捕捉能穿透厚物質的μ子。
亮度(luminosity):不是「有多光」,而是「有多繁忙」
碰撞產生事件的速度,取決於兩樣東西:碰撞的「截面」(cross section,理解為遇上的機率大小)和「亮度」(luminosity)。它們的關係很簡單:事件率 R = L × σ。亮度越高,像十字路口車流越密,互撞的機會就越高。提高亮度的方法包括把束團做得更緊、更準對焦,或增加束團數量。不過太緊的束團會帶來束流—束流的電磁擾動,也需要精密控制。
一秒4000萬次的取捨:觸發(trigger)與數據洪流
LHC 的束團交會頻率可達 40 MHz,也就是每秒四千萬次潛在事件。如果全部存檔,資料量會把世界的硬碟瞬間填滿。於是每個實驗都設計了多級觸發系統(trigger):
- 硬件級觸發(Level-1):在數微秒內挑選出「像樣」的事件,把速率從 40 MHz 降到約 100 kHz。
- 高階觸發(HLT, High-Level Trigger):用軟件在大型運算叢集上做更精緻的重建,最後以約 1 kHz 寫入磁碟。
數據經由世界各地的計算資源處理與分析,這個分層網絡叫作「全球 LHC 計算電網」(WLCG, Worldwide LHC Computing Grid),從 CERN 的 Tier-0 出發,分發到數十個國家/地區的 Tier-1 與數百個 Tier-2 中心。包括香港在內的研究團隊也參與其中,進行資料處理、軟件開發與物理分析。
我們在找什麼?從希格斯到未知新物理
LHC 最著名的成果之一,是與前代實驗一起鋪路,最終在 2012 年由 ATLAS 與 CMS 宣告發現希格斯粒子,確認了標準模型中賦予粒子質量的機制(希格斯機制)。之後多年,物理學家量度它與頂夸克(top quark)、W/Z 玻色子、光子等的耦合(couplings),檢查是否與標準模型精準吻合,或出現微妙偏差。
但 LHC 的任務不止於驗證既有理論,還要尋找超越標準模型(BSM, Beyond Standard Model)的現象,例如:
- 超對稱性(SUSY):為何希格斯質量這麼「輕」?是否有新的對稱性在背後保護?
- 暗物質(dark matter)候選:能否在碰撞中產生不帶電、逃離探測器的粒子,留下「缺失能量」(missing energy)的信號?
- 額外維度(extra dimensions)或複合希格斯(composite Higgs)的跡象。
- 罕見衰變與味物理(flavour physics)的破壞:例如 LHCb 對 B 介子衰變的精密測量,測試勒普頓普適性(lepton universality)等。
- 重離子物理:早期宇宙的夸克-膠子等離子體(QGP)之黏度、能量損失與集體流動行為。
工程上的「魔法」:對準、準直與安全
把兩束直徑細如頭髮的質子束,在數十公里後準確對焦到毫米級交會點,需靠無數校準與回饋控制。幾個關鍵機制:
- 準直(collimation):用一系列吸收塊把偏離的粒子「刮走」,避免打到探測器或磁鐵,造成損壞。
- 束流傾倒(beam dump):若系統偵測到異常,會把整束能量導向專門設計的石墨/金屬結構緩衝器,安全釋放數百兆焦的能量。
- 淬熄防護(quench protection):超導磁鐵若局部升溫失去超導性(淬熄),需在毫秒內分散儲存能量與導出電流,避免局部熱爆。
- 蟹形腔(crab cavities):在高亮度升級中,利用特殊 RF 腔把束團在碰撞前「橫向傾斜」,相當於讓兩隊人馬側身互過,提升有效重疊。
2008 年 LHC 曾因磁鐵接點失效導致氦氣洩漏而受損,自此全面升級電氣與防護系統。今天的運行在嚴格的保護邏輯下進行,穩健得多。
常見疑問:會不會造出「黑洞」吞噬地球?
這是經典迷思。即使在某些理論中,超高能碰撞可能產生極微型且瞬逝的「微黑洞」,它們也會透過霍金輻射(Hawking radiation)在極短時間內蒸發,不具危險性。更關鍵的是,宇宙線(cosmic rays)帶著比 LHC 更高的能量,不停地撞擊地球與其他天體,億萬年來毫無異常。如果這種碰撞有危險,我們的星球早已不在。國際獨立評估也反覆確認 LHC 運行安全。
為何要用「環形」,而不是一條直線?
環形加速器可以讓粒子「繞圈」多次,逐步加能,並重複使用相同的 RF 腔與磁鐵,整體更經濟。不過帶電粒子在彎轉時會發出同步輻射(synchrotron radiation)。對輕質的電子,輻射損耗很大,所以高能電子對撞機更偏好線性設計;而質子較重,輻射較小,環形仍然可行,於是 LHC 採用環形設計。
LHC 與日常生活的連結
雖然我們不會在超市遇到希格斯,但 LHC 推動的技術轉移十分實在:
- 醫學影像與放療:粒子探測器技術轉化到 PET、CT 的高效感測,粒子治療(proton therapy)亦與加速器工程密切相關。
- 超導與冷凍技術:工業級的超導線材、低溫工程提升了供應鏈和應用水平。
- 計算與大數據:為應付海量數據,CERN 與夥伴推動了分散式運算與高效數據管理,催生與強化了多種開源技術。
香港的科研社群亦長期參與 LHC 的合作計畫,從硬件研發到數據分析,與全球團隊一起培養人才、推動創新。
高亮度時代與更遠的未來
LHC 正在逐步走向高亮度升級(HL-LHC, High-Luminosity LHC)。目標是在 2030 年代累積約 3000–4000 fb^-1 的碰撞數據,等於把樣本量提升數倍,使罕見過程不再遙不可及,並把希格斯性質測得更精準。為此,需要更強的對焦四極體磁鐵(如 Nb3Sn 超導技術)、蟹形腔、新的準直系統與升級的觸發/讀出電子學。
再往後,社群正討論下一代設施,例如「未來環形對撞機」(FCC)構想,可能是一條約 100 公里的隧道,先運行電子-正電子(e+e−)對撞機(FCC-ee),再升級為百 TeV 級的強子機(FCC-hh)。也有人積極研究 μ 子對撞機(muon collider),有望把高能與高效率結合。這些路線各有工程與物理挑戰,但共同目標一致:把我們的「能量顯微鏡」推向更清晰的極限。
一場與自然的長談
LHC 不只是巨型機器,它是一場跨越國界、跨學科的集體行動。工程師讓超導磁鐵在宇宙最冷的溫度穩定工作;控制專家把粒子束像手術刀般對準;分析人員在數據海洋中尋找稀有信號;理論學家寫下方程式,預告我們可能看見的浪花。當希格斯被發現,我們確信了標準模型的一塊關鍵拼圖;當觀測與理論吻合或偏離時,我們都在學習——學習自然的語法,也學習謙卑地提問。
對香港的你我而言,或許日常感受不到地底 27 公里之外的震動。但每當我們想起一個簡單的問題:「世界最根本的樣子是怎樣?」LHC 就像替我們打開了一扇門。無論下一顆新粒子何時出現,這台把宇宙濃縮的環形實驗室,已經把我們的視野推向更深更細,並讓未來一代又一代的好奇心,有了更堅固的起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