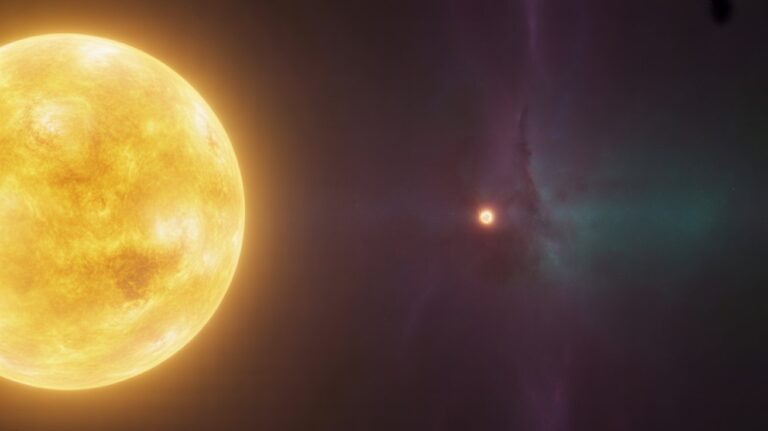看見宇宙的第一縷光:詹士韋伯太空望遠鏡是怎樣改寫天文課本的?
想像一下,你走進一間燈光極暗的房,手上拿著一部對紅外線特別敏感的相機,能看見肉眼看不到的微弱熱光。你不但能看見角落裡剛熄滅不久的蠟燭殘光,還能透視薄霧後面的人影。詹士韋伯太空望遠鏡(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,簡稱 JWST)就像這部「宇宙紅外線相機」,把宇宙最早期、最微弱、被塵埃遮蔽的光,一點一滴地收集起來,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看清宇宙嬰兒期的面貌,以及恆星與行星誕生的現場。
為什麼需要 JWST?哈勃望遠鏡不夠嗎?
很多香港朋友會問:哈勃太空望遠鏡(Hubble)不是已經很勁了嗎?當然,哈勃在可見光與近紫外線的觀測上無可取代,也對宇宙學做出巨大貢獻。但宇宙在「最早期」發出的光,經過上百億年的宇宙膨脹,被「拉長」成紅外線(Infrared)。同時,恆星形成區域裡有大量星際塵埃(Dust),會擋住可見光,卻較容易讓紅外線穿透。這兩個原因,使得要看得更早、更深、更內部,我們就需要一部「紅外線主導」的望遠鏡,且感光度要超高、噪音要極低。
JWST正是為此而生。它的主鏡直徑達到 6.5 公尺,比哈勃的 2.4 公尺大很多,收光能力(光子收集)大幅提升。更重要的是,它的科學儀器專注於近紅外(Near-Infrared, NIR)到中紅外(Mid-Infrared, MIR)波段,能觀測到宇宙最遙遠星系的「紅移」(Redshift)後的光,也能透視塵埃雲中的恆星育嬰室。
飛去哪裡?為什麼不繞地球?
哈勃在低地球軌道(LEO),方便太空梭維修,但地球很亮、很暖,對紅外線觀測不是理想環境。JWST被送往日地系統的第二拉格朗日點(L2),距離地球約 150 萬公里,位於地球背向太陽的一側。這個位置的好處是:
- 熱與光源在同一方向(太陽、地球、月亮大致在同一側),便於用遮陽罩(Sunshield)阻隔。
- 熱穩定環境更佳,避免紅外線儀器被自身或外界熱輻射「照花」。
- 可長時間持續指向同一片天空,提升深度觀測效率。
當然,L2不是「完美平衡點」,JWST需要定期進行「軌道維持」(Station-keeping)微調,保持在 L2 周圍的晝面軌道(Halo orbit)。
像金色花瓣的主鏡:設計有何門道?
JWST最標誌性的外觀,就是由 18 塊金色六邊形鏡面組成的主鏡。這些鏡片由鈹(Beryllium)製成,表面鍍上一層超薄黃金,因為金對紅外線反射效率高。六邊形拼接(Segmented mirror)有幾個關鍵優點:
- 可折疊發射:6.5 公尺的主鏡太大,必須在火箭整流罩內摺疊,入軌後再展開。
- 可精準校準:每片鏡都有微動致動器(Actuators),能以納米級(Nanometer)改變位置和曲率,把 18 幅影像疊合成一個完美焦點。
- 熱穩定佳:鈹在極低溫依然堅挺且質輕。
這種分段主鏡配合波前感測(Wavefront sensing)與相位校正(Phasing),讓 JWST在太空中「自己對焦」。人手無法去到 L2維修,所以一切校準都靠遙控算法與精密機械。
巨型五層遮陽罩:讓望遠鏡「冷到發抖」
紅外線觀測有一個殘酷現實:任何東西只要有溫度,就會發出紅外線,包括望遠鏡自己。要看見微弱的宇宙紅外線,儀器本身必須冷得近乎「不發聲」。JWST的解法是「被動冷卻」(Passive cooling)。它的五層遮陽罩像一把超巨型的銀色摺扇,層與層之間逐級把太陽與地球的熱輻射反射與散熱,最冷那一面可降到約 40 K(-233°C)。
這樣的低溫讓近紅外儀器(NIRCam、NIRSpec、FGS/NIRISS)能以極低熱噪音工作。但對中紅外儀器 MIRI(Mid-Infrared Instrument)而言,還要更冷,於是配備了機械式冷凍機(Cryocooler),把 MIRI 降到約 7 K。這種「被動+主動」雙軌冷卻,使 JWST能在 0.6–28 微米的波段維持高靈敏。
四大科學儀器:各司其職
JWST搭載四套主要科學儀器,每套像一部「專用鏡頭」,合力完成多面向科學任務:
- NIRCam(Near-Infrared Camera):主力成像儀,負責高靈敏近紅外攝影,也是波前感測與校準的關鍵。擅長拍「超深場」(Ultradeep field)、恆星育嬰室、近鄰星系結構等。
- NIRSpec(Near-Infrared Spectrograph):近紅外光譜儀,能同時對上百個目標取光譜,靠的是微型快門陣列(Micro-Shutter Array, MSA),像一幅可編程的「光學百葉窗」。光譜讓我們量度紅移、金屬量(元素豐度)、恆星形成率等。
- FGS/NIRISS(Fine Guidance Sensor / Near-Infrared Imager and Slitless Spectrograph):FGS負責精準導星,讓長時間曝光不會「手震」;NIRISS則提供無狹縫光譜(Slitless spectroscopy)與特殊模式,如觀測系外行星的凌日光譜。
- MIRI(Mid-Infrared Instrument):中紅外成像與光譜,對冷塵埃、分子雲、原行星盤(Protoplanetary disks)及高紅移星系的塵輻射特別敏感。
看見多早?「宇宙黎明」與高紅移星系
宇宙年齡現今約 138 億年。JWST的其中一個核心目標,就是捕捉「第一批星系」在宇宙不到 5 億年時的樣子,這段時期常稱為「宇宙黎明」(Cosmic Dawn)與「再電離時期」(Epoch of Reionization)。
當我們說「看到 132 億年前的星光」,其實是指光在路途花了 132 億年才抵達我們。宇宙膨脹令波長被拉長,紅移值(z)很高,例如 z > 10 的星系,其主要光譜特徵(例如 Lyman-α 斷裂)已被移到近紅外甚至中紅外。這剛好落在 JWST的主場。
JWST早期科學就發現了一批極高紅移候選星系,部分經光譜確認達 z≈13–14。這些對宇宙學模型是「壓力測試」:這麼早期的星系為何能長得這麼快、這麼亮?是恆星形成效率很高,還是塵埃與恆星族群的性質不同?天文學家正用 NIRSpec與MIRI光譜資料,拆解這些星系的恆星年齡、金屬量與氣體動力學。
塵埃幕後的育嬰室:恆星誕生與原行星盤
如果你曾在霧天開車,會知道近燈比遠燈更好用,因為霧會散射可見光;紅外線就像「穿霧燈」。星際塵埃對可見光不友善,卻讓紅外線有機會透視。JWST利用這點,為我們打開恆星形成區的「後台」。
在獵戶座分子雲、船底座等地區,JWST拍到原行星盤中的空隙與環帶,並以 MIRI偵測多環芳香烴(PAHs)與各種分子發射,追蹤塵埃顆粒成長、冰(H2O、CO2、CH4等)沉積與化學演化。這些觀測能回答:行星在多長時間尺度內成形?水與有機分子如何由星際雲一路被送進行星系統?這些都是理解「我們從哪裡來」的關鍵線索。
系外行星的大氣:用「指紋」讀出化學成分
香港人愛旅行,過關要查身份;光也一樣,經過行星大氣會留下「通關章」。當行星從母恆星前方掠過(凌日,Transit),星光一部分穿過行星大氣,某些波長被分子吸收,形成吸收線;若行星從背後走到恆星後面(次凌,Secondary eclipse),我們能用差值量出行星自身熱發射。這些方法統稱「凌日光譜學」(Transit spectroscopy)。
JWST的近紅外與中紅外儀器能同時量度水(H2O)、二氧化碳(CO2)、甲烷(CH4)、一氧化碳(CO)、硫化氫(H2S)等分子的特徵吸收。早期觀測已在多顆熱木星(Hot Jupiters)與迷你海王星(Sub-Neptunes)的大氣中看到清晰分子訊號,甚至偵測到雲霧分佈與溫度層結。這類資料能反推行星的形成地點(例如在冰線內或外形成)、遷移歷史與內部能量收支。
至於類地行星(地球大小)的氣氛偵測更具挑戰,因為訊號微弱且恆星活動會干擾。JWST正聚焦於繞行小型、較暗的紅矮星(M矮星)系統,如 TRAPPIST-1,嘗試在多次凌日疊加下逼近可檢測門檻。即使未能立刻看到「生命指標」,我們也在快速建立對岩石行星大氣的基本統計。
引力透鏡:用宇宙當望遠鏡
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告訴我們,重力會彎曲時空,光走過質量集中的地方會被偏折。當前景的星系團像是一塊「宇宙放大鏡」,會把更後方的微弱星系放大、拉長成弧。JWST把這種「引力透鏡」(Gravitational lensing)用到極致,能把本來太暗看不見的早期星系放大到可測量的亮度,甚至解析出內部結構。
這種自然加持的「光學增益」不但幫助我們看到更早期的天體,也讓天文學家能測試暗物質(Dark matter)的分佈,因為透鏡影像的形狀與放大倍數會對前景質量分佈十分敏感。
數據不是 JPEG:背後的校正與管線
你在新聞看到的 JWST 圖片絢麗奪目,但原始資料其實像「灰黑的生相片」。從光子打在探測器(Detector)開始,到你我看到的彩色圖,需要一條嚴謹的資料處理管線(Data reduction pipeline):
- 探測器效應校正:包括暗電流(Dark current)、非線性、壞像素、串擾、1/f 噪音等。
- 背景與雜散光處理:扣除天空背景、熱輻射貢獻與光學鬼像(Ghosts)。
- 光譜抽取與通量定標(Flux calibration):把像素轉成實際能量與波長,並校正儀器響應。
- 成像合成(Drizzling/Resampling):把多張偏移拍攝的影像拼合,提高解析度、減少雜訊。
最後的彩色圖多半是「指派色」(Color mapping):把不同濾鏡或波段賦予紅、綠、藍通道,再經過對比拉伸與動態範圍調整。這種做法不等於「造假」,而是把人眼看不到的紅外線訊息,翻譯成我們能理解的顏色語言,同時保留科學量度所需的數值版本。
工程賭注:一次性展開的風險與成功
JWST是一場高風險工程。發射後需完成超過 300 個單點失敗(Single point of failure)的展開與鎖定步驟,包括遮陽罩放開、拉緊、鏡面展翼翻開、次鏡架伸出、每片鏡面初步定位等。任何一道卡住,都可能前功盡棄。團隊透過冗餘感測、地面演練與分段驗證,把風險壓到最低。2021 年底發射後,一切展開順利,接著是數月的冷卻、對焦與儀器調試,才正式開始科學運作。
在成本方面,JWST耗時超過二十年、投入數百億港元級別資金,這常引發公共討論:值不值得?從科學輸出與技術外溢(例如紅外探測器、低溫工程、精密控制)來看,它像一個「前沿平台」,帶動整個學術與工業鏈的升級。
它和我們有什麼關係?從宇宙到生活的連結
有人會說,宇宙很遠,跟生活有何關係?其實,JWST背後的很多技術,會回流到地面應用:高靈敏紅外線感測可用於醫療成像、環境監測;低溫工程與熱控技術改良航天與晶片散熱;資料處理算法推進電腦視覺與大數據分析。而從文化角度,JWST為人類建立共同的宇宙圖像,像一面鏡子提醒我們:在 138 億年的時間軸上,地球文明只是剛剛「打開燈」,更需要謙卑合作。
常見迷思澄清
- JWST能拍到「外星人」嗎?——不能直接「拍到外星人」。它能分析系外行星大氣,尋找某些化學指標(如不平衡氣體組合)可能暗示生物過程,但這需要多項證據交叉驗證,遠非一張照片能定案。
- 為什麼圖像是金色或彩色?——因為觀測的是紅外線,人眼不可見。科學家用不同波段賦色,既方便展示不同物理過程,也讓我們在可視範圍理解結構。
- JWST會取代哈勃嗎?——兩者互補。哈勃在紫外與可見光仍然無可替代,JWST在紅外線極致敏感。把兩者資料合併,能得到跨波段的全景。
香港觀星迷可以怎樣參與?
即使不做研究,你也能參與 JWST 的成果探索:
- 公眾資料庫:NASA/ESA 的 Mikulski 天文資料檔案館(MAST)會在專案保留期後公開數據。你可下載 FITS 檔,嘗試用免費軟件(如 ESA 的 ESASky、SAOImage DS9、astropy)做基本處理。
- 公民科學:平台如 Zooniverse 不時開設與 JWST 相關的影像分類專案,幫助研究團隊尋找弧形透鏡影像、原行星盤結構等。
- 本地講座與線上分享:留意本地天文學會、科學館與大學的公開講座,許多都會解讀最新 JWST 發現。
下一步:從「第一光」走向精細物理
JWST的早期驚喜已把我們的問題清單越寫越長:為何早期星系這麼「成熟」?第一代恆星(Population III)是否已留下金屬蹤跡?黑洞在宇宙嬰兒期如何長得如此迅速?未來數年,天文學家會用更長的曝光、更精細的光譜與統計樣本,從「發現型」科學過渡到「測量型」科學,建立穩健的宇宙演化時間線。
同時,系外行星大氣光譜將從熱木星,推進到溫暖的迷你海王星、超級地球(Super-Earths),甚至嘗試對岩石行星的二氧化碳與水蒸氣作上限約束。配合地面超大望遠鏡(ELT、TMT、GMT)與未來的羅曼太空望遠鏡(Roman Space Telescope),我們正走向一個「多平台協同」的黃金年代。
結語:把宇宙時間放進我們的口袋
JWST讓我們第一次把宇宙最初幾億年的「微光」收進口袋,把被塵埃遮住的恆星誕生劇場打亮,也把遙遠行星天空中的分子「指紋」放到顯微鏡下。對於在香港這樣繁忙城市生活的我們,也許最重要的,是它帶來的視野轉換:當你在維港邊抬頭望向夜空,那些昏黃路燈之外的黑暗,其實充滿訊息,只是需要合適的眼睛去看。JWST正是人類為自己打造的一雙新眼,讓我們在廣闊宇宙中找到位置、提出更好的問題,並在追問的路上,學會更耐心、更專注,也更彼此相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