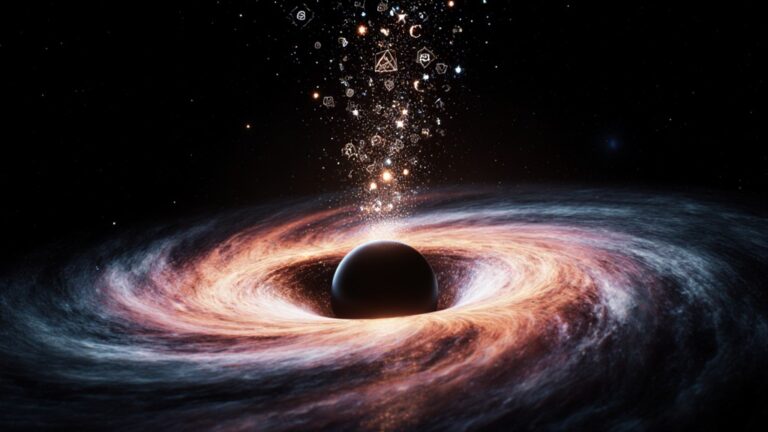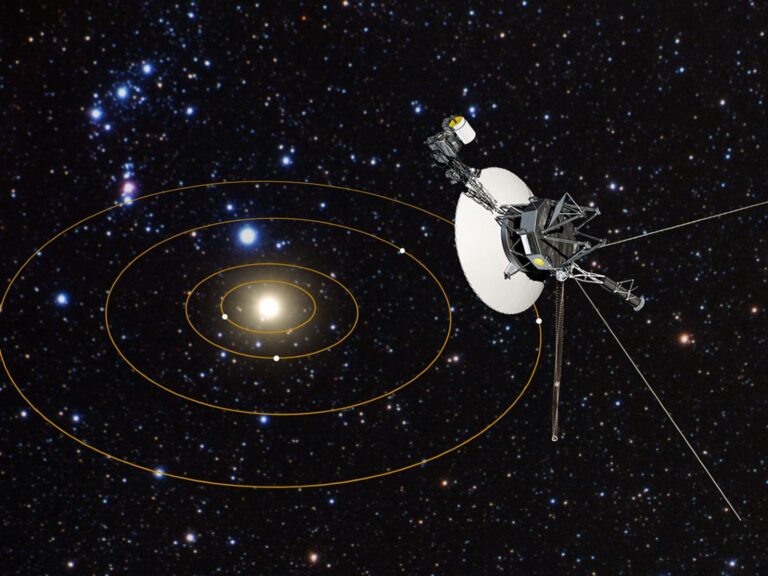甚麼是SETI計劃?
一個半世紀來,人類一直有個好奇:那些天上的光點背後,有沒有另一群像我們一樣會發問、會建造、會發出訊號的「鄰居」?SETI(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,地外智慧搜尋)就是用科學方法,嘗試回答這條問題的長期計劃。它不是獵奇,更不是電影橋段,而是一個集天文、工程、數學、電腦科學、甚至社會學於一身的跨學科探索。
為何要找?從「是否有鄰居」到「我們是誰」
對香港人來說,住樓聽到隔壁開收音機,不一定代表你認識對方,但至少證明「有人」。SETI 的基本動機也類似:宇宙極大,星星極多,按天文數據計算,行星很常見,適居帶(temperate zone)行星也不罕見。問題是:有沒有文明達到可以被我們「聽見」的程度?
這不是浪漫問題,而是科學問題。生命是否普遍、智慧是否持久、技術文明能否避免自我毀滅,都是關於我們自身未來的鏡子。SETI 嘗試以可被驗證的方法,去測試「我們不是唯一」的假設。
SETI 是甚麼?不是太空探險隊,而是訊號偵測隊
SETI 並不派人去外星,也不專找「飛碟」。它主要做三件事:
– 電波搜尋:用射電望遠鏡(radio telescope)「收聽」天空,尋找疑似人工的無線電訊號。
– 光學搜尋:用光學望遠鏡尋找激光(laser)的短閃或脈衝,因為高功率激光是遠距離通訊的可能手段。
– 其他技術跡象(technosignatures):例如尋找超大工程(如戴森球 Dyson sphere)造成的紅外過量輻射,或行星大氣中的非自然化學痕跡。
把它想成一個超大型「掃台」:從 FM、AM 到數碼頻道逐個掃,不同的是,宇宙的頻道遠比你家的收音機多,噪音也多得多。
德雷克方程:先問「有幾多台值得掃」
1961 年,天文學家 Frank Drake 提出德雷克方程(Drake Equation),用來框架式地估算銀河系內可通訊文明的數量 N:
N = R* × fp × ne × fl × fi × fc × L
– R*:每年產生恆星的速率
– fp:有行星的恆星比例
– ne:每個行星系平均有多少適合生命的行星
– fl:生命實際出現的比例
– fi:生命進化為智慧生命的比例
– fc:能釋放可被探測訊號的比例
– L:文明釋放訊號可持續的時間
這不是計分機,而是「提問地圖」。前半部(R*、fp、ne)近年因開普勒(Kepler)與 TESS 任務而得到較好約束:行星很常見,地球大小行星在適居帶並不少見。後半部(fl、fi、fc、L)仍然不確定。SETI 的每一次搜尋,都在嘗試對 fc 和 L 這類未知數「投光」。
為何鎖定「微波窗」與 1420 MHz?
宇宙不是每個頻率都清晰。地球大氣在某些頻段很透明,宇宙背景噪音也較低,形成所謂的「微波窗(microwave window)」。1420 MHz 是氫原子自旋翻轉線(HI 21-cm line)的頻率,宇宙充滿氫,這個頻率對任何做過基礎物理的文明都具有「自然地標」意義。於是有學者提出,「如果要寄一封宇宙共通的電郵,用這頻段可能最不容易錯過」。
當然,SETI 不會只聽一個頻率,而是選擇整段頻譜(frequency spectrum)做高解析度掃描,因為「鄰居」未必用我們想像的頻道,亦可能用窄帶(narrowband)或掃頻(chirped)設計來穿透噪音與多普勒效應(Doppler effect)。
怎樣分「人造雜訊」與「可能是外星」?
住在香港最知噪音煩擾:電車、電鑽、Wi‑Fi、藍牙。射電天文一樣,地面電訊與衛星訊號是巨大的干擾(RFI, radio-frequency interference)。SETI 的「清場」功夫非常講究:
– 多天線同時監聽:真正來自星空的信號會在不同天線以相對一致的延遲與方向出現;地面干擾多半同時「通天」或指向性不同。
– 盲測與追蹤:疑似信號會多晚、跨日、跨月重測;若訊號不隨地球自轉而有預期的多普勒漂移,通常可判為地面或近地來源。
– 對比「開/關目標」:把望遠鏡在目標與空白區域間來回切換,若信號只在目標方向出現才是可疑。
– 頻譜特徵分析:人工文明若想被聽到,最省能的方法是極窄頻帶訊號;自然天體(如脈衝星)雖有規律,但頻寬與調製特性不同。
2017 年著名的「Wow! 信號」再分析與多個「詭異」個案,多數最終指向人類衛星或儀器效應。這並非壞事,因為科學的嚴謹就在於不把噪音當訊號。
硬件陣容:從 Arecibo 到 Allen Array,以至「百億顆手機」的運算力
– Arecibo(波多黎各):曾是地球上最大的單口徑射電望遠鏡,既能發射也能接收。它在 1974 年向球狀星團 M13 發射著名的 Arecibo 訊息,更多則用於雷達行星科學。2020 年坍塌令人惋惜,但它啟發了整整一代 SETI 與行星研究。
– Green Bank Telescope(美國):世界最大可轉向單碟射電望遠鏡,是「Breakthrough Listen」的主力之一。
– Parkes / Murriyang(澳洲)、MeerKAT(南非)、FAST(中國貴州):都是當代一流的射電耳朵,FAST 尤其在窄帶搜尋上具優勢。
– Allen Telescope Array(ATA,美國):多天線陣列(interferometric array)專為 SETI 和射電天文設計,可同時監聽多個方向,像一雙「分得開注意力」的耳朵。
在運算方面,SETI@home 曾把全球志願者的電腦閒置時間化為分析能力,等於「百億顆手機」一起幫手。雖然項目已於 2020 年暫停派工,但分散式運算的概念被許多天文與生物項目沿用。
突破聆聽:Breakthrough Listen 的系統化時代
2015 年,物理學家 Yuri Milner 支持的「Breakthrough Listen」計劃,投入一億美元資金,目標是系統、深度地掃描鄰近百萬顆恆星、銀河中心與數十個近鄰星系,涵蓋從 1 到數十 GHz 的頻段。其特點:
– 高動態範圍與超高頻譜解析度:能在巨量噪音中抓到如髮絲般窄的訊號。
– 公開數據(Open Data):數百 PB 級數據逐步開放,鼓勵外界用新演算法再挖寶。
– 算法創新:廣用機器學習(machine learning)與異常檢測(anomaly detection),自動從海量頻譜中挑針。
這種「把海撈針改為把針變粗」的策略,讓 SETI 從零散的觀測,進入可重複、可審核、可擴展的工程級搜尋。
光學 SETI:為何要找激光閃光?
光學 SETI 針對的是 ns 到 μs 等級的超短激光脈衝。理由很簡單:如果你要對 1000 光年外的鄰居「眨眼」,用超亮、超短的激光最省能也最醒目。實作上,天文台會用快速光電倍增管(PMT)或雪崩光電二極體(APD)配合時間標記器,尋找與背景星光明顯不同的「針尖閃動」。
這些搜尋同樣要面對衛星反光、雷射測距、甚至地面雷射表演的干擾,因此也用到多站同時偵測與交叉驗證。近年亦有把光學與射電同步監聽的「多信使(multimessenger) SETI」策略:如果同時在兩個波段看到可疑事件,可信度更高。
技術跡象的新視野:戴森球、紅外過量與工業化大氣
– 戴森球(Dyson sphere):假想中的巨構,包圍恆星以收集能量。完整球殼不現實,但 Dyson 群(Dyson swarm)或軌道太陽能的總效果,可能讓該恆星在中紅外(MIR)有異常過量輻射。WISE 與 Spitzer 的全天紅外巡天被用來尋找這類候選。
– 人造大氣特徵:若在系外行星的透射光譜中看到氯氟碳化物(CFCs)等純工業分子,或高度不平衡的化學組合,可能是工業活動或大規模能源利用的副產品。JWST 與未來的超大口徑望遠鏡可望提供敏感度。
– 夜面光:極難,但原理直觀——若一顆行星的「夜面」有異常人造光度,可能是城市級照明。不過現階段技術上遠未到可行尺度。
為何尚未「聽到」?費米悖論與多重解釋
費米悖論(Fermi Paradox)問的是:如果文明常見,為何我們未見其跡?常見解釋有:
– 信號錯配:他們不用我們聽的頻率、調製方式,或只在短時間發射。
– 距離與能量:即使在銀河內,訊號強度以平方反比衰減,想被聽見需要巨大功率或高度指向性,機會小。
– 時間窗問題:L 或許很短——文明在可被偵測的階段只維持幾百或幾千年,錯過就沒有了。
– 沉默策略:高度文明可能刻意保持無線電靜默,避免風險,轉用纖維、量子密鑰或其他「不外洩」通訊。
– 自然稀有與篩選:fi 或 fc 本身極低,能跨越技術與社會挑戰而長存的文明不多。
SETI 的策略因此是「廣覆蓋+深掃描+長時間」,最大化撞到「時間窗重疊」的概率。
META:從搜尋到科學方法的示範
SETI 不是單向消費浪漫的工程,它對科學方法本身有貢獻:
– 嚴格的假陽性控制:每一則「疑似」都必須有可重現的觀測、可被他台獨立驗證。
– 開放數據與可重複性:讓外界可再分析,減少主觀偏見。
– 跨學科算法與硬件創新:把高頻數據壓縮、時間頻譜分析、RFI 建模、異常偵測等推到新境界,回饋到其他天文與通訊領域。
社會與政策:若真的收到,怎辦?
國際天文學聯合會(IAU)與 SETI 社群有「首次檢測後程序」指南:
– 多重獨立驗證,公開方法與數據。
– 通知國際機構,避免單點發布引發混亂。
– 暫不回傳(reply)任何訊號,先經全球共識與倫理討論。
這些不是為了煞有介事,而是避免把自然或人為假訊號當真,也避免單一團隊代表全人類行動。
SETI 的未來:更廣、更快、更聰明
– SKA(平方公里陣列):建成後將把靈敏度與掃描速度推到新層級,對窄帶訊號敏感度大幅提升。
– 全頻寬化:從 kHz 到 tens of GHz 的同時觀測,減少「錯失」機會。
– 自動化異常工廠:把機器學習與物理先驗結合,建立可解釋的 AI 檢測流程,降低假陽性。
– 多信使整合:射電、光學、紅外以至高能波段的同步搜尋,建立事件級「證據鏈」。
可以預期,未來十到二十年,我們對「宇宙是否沉默」的統計界線會收窄許多:若仍未有發現,意味著 fc×L 的上限會被壓得更低;若有蛛絲馬跡,將是科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。
結語:用科學的方法,守一份耐心
SETI 像在嘈雜的城市以最敏銳的耳朵,找一段可能存在的旋律。它需要耐心、需要工程與理性的執拗,也需要群眾的參與和透明的方法。是否「有鄰居」也許仍需時間,但在搜尋的過程中,我們已學懂更精準地觀天、在噪音中辨識模式、以及用可檢驗的方式回答最大的問題。